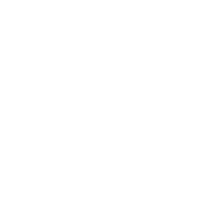2002年2月7日,这和过去43年的每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也是这,我毫无征兆地被诊断患有卵巢癌。我仿佛像是从悬崖上掉了下来,缓慢地做自由落体运动,但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着陆。

Patti Branowicki
和往常一样,我的工作日程仍然是从早上7:30到下午5:30参加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然而,为了搞清楚我为什么会出现间歇腹痛的原因,我不得不抽出一些时间到我的妇科医生那里接受常规检查。经过检查,医生告诉我,她觉得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不过,这需要做超声波检查进行核实。虽然医生的担忧很明显,但是我依然相信,没什么可值得担心的。毕竟,我以前从没有得过重病,而且我们也没有癌症家族病史。因此,在做超声波检查之前,我还回到儿童医院参加了一个会议。
做完超声波检查后,我的妇科医生让我立即回到她的办公室。候诊室里非常安静,护士迅速地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当医生让我给我的丈夫打电话时,我觉得,一种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感觉朝我袭来。我的丈夫赶到这里至少需要一个小时,所以,没有耐心等待的我请求医生告诉我实情。医生并没有对我隐瞒,我可以看见她在说,但我却听不到她在说什么。我认为,我们的大脑只接收我们有能力面对和处理的信息。从医生告诉我病情的那一刻起,我觉得我再也无法面对和处理我所听到的信息了。我的朋友和同事Susan Shaw是儿童医院临床手术的主任。我打电话给她,让她过来帮我确认一下大多数人都害怕听到的消息:“你可能得癌症了。”
我完全被这个消息给吓懵了。Susan和我回到儿童医院后立即给Stephen Sallan打电话。医学博士Stephen Sallan是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的办公室主任。他说,如果我的卵巢癌确诊了的话,他可以把我推荐给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的医学博士Ursula Matulonis。除了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我也从没想过去其它的医院接受治疗。
几天后,医生给我做了一次手术,手术的结果证实了我的癌症,而且还是三期卵巢癌,癌症已经从我的卵巢转移到了其它部位。然后,医生给我做了全子宫切除术。从此,我的生命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斥着手术绝经的各种症状以及癌症治疗带给我的心理忧虑和生理影响。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参加了由Matulonis博士负责的临床试验,并接受了我的化疗。接下来的7个月是9个周期的化疗,在此期间,我接受了三种不同的药物治疗方案。
不管是来自儿童医院的同事,还是来自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的医生和护士,他们的表现总是充满了神奇的力量。我记得,我曾对儿童医院的总护士长Eileen Sporing说过,情况不是很好,我不确定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我是不是还可以回来。她郑重地、不带一丝犹豫地告诉我:“你一定会回来的。我会一直负责你的工作直到你回来为止。”医学博士David G. Nathan是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的名誉院长,他曾劝告我:“不要向右看,不要向左看,眼睛直视前方的目标。我们需要你回来。”
在我人生黑暗的时刻,这些劝告、支持、鼓励的话语,这些祝福的贺卡、电话和礼物让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打败癌症的艰难抗争中。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每个人都很,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我很荣幸,我可以认识和结交这些十分出色的人们。
我知道,一个癌症治疗方案的实施是非常严谨的,所以,在治疗之初,我停下了手里的工作,专心接受治疗。我本打算至少请假6个月。然而,做完全子宫切除术后的几个星期,人们开始给我打电话讨论工作的相关事宜,还把备忘录和文件送到家里让我看。到5月份,我决定先以兼职的方式重返工作岗位,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把工作带到家里做。其实,对我来说,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工作才是好的药,因为它帮我完成了从“癌症患者”到“癌症生存者”的成功转型。
【盛诺一家】成立于2011年,是国内权威的海外医疗咨询服务机构,提供出国看病、全球专家远程咨询、日本体检等服务。
海外医疗服务为什么选择盛诺一家?
如果您或家人想了解海外就医方案?
📞 请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855-7089 或通过
🌐 盛诺一家官网 预约咨询,获取专业建议,开启全球精准医疗之路。
 15
15
 1000+
1000+
 15
15
 8000+
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