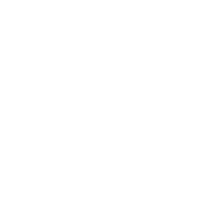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开始讲述这个故事,但是我知道我必须把我过去几年的人生经历给写下来。在过去几年,我们犹如坐过山车一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大事件。

Edie和Noble
2005年4月,当我和我丈夫Noble、我们家的宠物狗Sam和宠物猫JoJo在Lincoln Rock州立公园宿营时,我怪异地感到一阵眩晕,不过很快好了,但后来又时不时地出现了轻微头晕,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1年。看了几位医生后,我被诊断出患有内耳病毒感染,医生说这种病会被治好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然而,到了2006年5月,我连正常走路都感到困难了—我的双腿不会正常工作了,而且这种情况日益恶化,以至于我不得不放弃打网球(1周3次)和跳爵士健身操(1周4至5次)。后,我只能借助手杖和在Noble的搀扶下四处走动。
从2006年夏到2007年1月,我在当地和西雅图看了好几位医生,其中包括四位不同的神经科医生。似乎没有人能够诊断出我的身体恶化是种什么病。现在,我左手的精细动作协调能力已受到影响,我说话有时候也发音不清,腿部僵硬让走路变得极其辛苦和困难。我做了一大堆检查—比你听说的还要多—MRI检查、CT脊髓造影术、骨骼扫描、血液检查、脊椎穿刺、视觉诱发电位检查(VEP)、肌电图检查(EMG)、脑电图检查(EEG)等等。我已经从一个非常健康、充满活力的人变成了一个残疾人。我的整个人生都改变了。
因为医生们似乎无法识别我的病,所以我和Noble后索性给它起了个名字ESCP(Edie's Spinal Cord Problem即Edie的脊髓疾病),这个名字不是医学术语。
在此期间,有位神经科医生对我说,我得了原发性进展型多发性硬化,然后西雅图的另外一位神经科医生终给我的诊断结果是德维克病或NMO(视神经脊髓炎)。这位神经科医生是根据MRI检查发现我的胸椎上有一个病灶而做出的诊断决定。他还将专门针对德维克病的血液检查样本发给Mayo Clinic,因为Mayo Clinic是治疗这种疾病的医院。但是,他补充说,即使Mayo Clinic发回来的结果是否定的,他也仍然认为我患的是这种病。他开始让我接受硫唑嘌呤消炎药治疗。
Mayo Clinic发回来的血液检查结果否定了德维克病诊断,虽然当地的神经科医生不同意Mayo Clinic的诊断结果,但是他也无法承诺其他任何确切诊断。Noble拿起电话联系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Mayo Clinic。Noble从他的全部调查结果中得知,Mayo Clinic的医生了解德维克病。
2007年3月19日,我们飞往罗彻斯特,去Mayo Clinic神经科接受为期一周的评估诊断。这是一次难忘的诊经历!我们首先看了两位医生,他们给我安排了一系列检查,在过去1年半(或者更多)的时间里,为了试图弄清楚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梅奥医生给我安排的检查我都做过了。在为期一周的检查结束时,我被告知我肯定没有患德维克病,但是我的确患有铜缺乏症,该病可引起脊髓问题,并且我可能还患有原发性进展型多发性硬化这一无法治疗的疾病。由于我没有患德维克病,所以医生让我停止服用硫唑嘌呤,转而让我开始服用铜补充剂。然后,医生还让我在离开罗彻斯特之前再接受一次血液检查,于是我在周五又做了一次血液检查。紧接着,周一上午,我接到了梅奥医生打来的电话。医生在电话中说,他们拿到了上次血液检查的结果,并对结果感到十分吃惊,因为血液检查结果表明我的血液中有一种影响脊髓和脑干的罕见GAD65抗体。和铜缺乏症一样,这种情况通过静脉注射类固醇和硫唑嘌呤长期治疗能治好。患有一种可治疗的疾病真是一件幸事。现在,梅奥医生认为原发性进展型多发性硬化的诊断是不大可能了。他们让我重新开始服用硫唑嘌呤和立即开始接受连续5天的类固醇静脉注射治疗,然后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每月接受一次类固醇静脉注射治疗。
自2007年以来,我多次前往罗彻斯特Mayo Clinic复诊。近的一次复诊是在今年夏天。我的医生(Pittock博士)说,他们本来只期望能稳定我的病情,但是我的病情出现了如此明显的好转,以至于在接下来的18个月到2年内我都无需再来Mayo Clinic复诊了。我们对梅奥医生的卓越治疗和协作表示万分感激,梅奥医生为我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治疗方案。我们发自肺腑地感谢Mayo Clinic。
下面发生的好事对我来说意味更多:
Noble于2006年1月7日退休,他在2006年1月11日接受了一次重大的背部手术。当时我之所以能够帮助他从手术中恢复过来,是因为那时我的病还未令我极度虚弱,我病的时候他又帮我到处走动。
Mayo Clinic指定给我看病的那位医生碰巧是2006年新近发表的一篇关于GAD65抗体标记检测的研究论文的作者。西雅图的医生是在1月份让我开始服用硫唑嘌呤的,所以在梅奥医生告诉我重新服用该药之前我只停药了三、四天。德维克病完全与我不相干了,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但是上帝把它除掉了。现在,我有了一个治疗这种罕见疾病和铜缺乏症的治疗计划。
一路走来,不乏机缘巧合之事。只简单提一下我们在Mayo Clinic的意外情缘吧。有,我们坐在候诊室等着见医生,对面房间里的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子起身向我们走来。她说,她注意到我们夫妇两个对待彼此非常有爱,所以她想知道我们是不是信徒。她还看见了Noble穿的衬衫前面的守约者徽标,她说她走向我们的时候她认出了这个徽标。对我们来说,这是多么甜蜜的惊喜和鼓励啊。我告诉她,在当天上午早些时候,她应该也看见我们在为走哪条路能到达我们要去的办公室而争论不休了!
给我做脊椎穿刺的护士用心倾听了我和我儿子之间的疏远与隔阂,因为她和她女儿之间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她写下了我推荐她看的一本书的名字,这本由Navigators Jerry和Mary White合著的“When Your Kids Aren't Kids Anymore”给了我莫大帮助。当她非常仔细地写下所有信息时,我知道她一定会明白我的用意。我们谈得非常愉快。我觉得她不是基督教徒,她肯定会从这本书中得到很好的建议和启发。
有一位医疗技师,当我对她说我在所有背部和脑部MRI检查过程中依靠做祷告、唱“Amazing Grace”和默默背诵《腓立比书》4章:6-7节来打发时间时,她看上去很惊讶。她说“冥想很有好处。”
当我们和梅奥的一位女医学博士坐在一起交谈时,她口述了她写的关于我的医生手记。我记得我们读过以前另外一位西雅图医生的手记,我读了之后非常高兴,因为他们说我是“一位讨人喜欢的、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的女性。”所以,我对她说,你可以在你的手记中也加上类似的话,她果真这么做了。我们都笑了。
在过去一年中,我有许多好朋友为我祈祷,陪我一起走过。有些朋友在教堂周一晚上的小组聚会上为我祈祷,有的来到我家为我祈祷,来自全国各地的亲戚和朋友祷告、发邮件、送贺卡、打电话等等,遥寄他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我的一位朋友甚至以我的名义定期禁食。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有多么关心和爱护我。这种谦卑的爱是上帝之爱。教堂的长者对我施坚信礼,给我傅油,这在我的生命中还是#1次。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鼓舞。
上周一晚上,在我对上帝祷告时,我收到了上帝传达给我的好消息,我终于明白了。我感谢这一段艰难的经历让我和上帝、和我的丈夫Noble、和我的许多好朋友的关系更亲密了。除此之外,我更加理解和同情残障人士了。上帝让我从他人身上感受到了我对爱的新认识。假如我能消除这段经历,我也不愿拿这段经历来换取任何其他经历。我只是在走我自己的人生之路,然而上帝却让我绕路而行,目的是让我学习一些新东西,让我更好地了解他。他在这些艰难时期教给我的东西可能是我在任何其他道路上都学不到的。现在,我知道该如何与遭遇相似问题的其他人一起分享上帝之爱了。我一次又一次地从艰难境遇中感受到了上帝之爱。我知道它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但它终闯入了我的内心,我将永远感谢这次的疾病遭遇和我在面对疾病时上帝给我的亲切关怀。不管我能否治疗康复,我都不会用这段经历换取任何事情。上帝一直在保佑我。
【盛诺一家】成立于2011年,是国内权威的海外医疗咨询服务机构,提供出国看病、全球专家远程咨询、日本体检等服务。
海外医疗服务为什么选择盛诺一家?
如果您或家人想了解海外就医方案?
📞 请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855-7089 或通过
🌐 盛诺一家官网 预约咨询,获取专业建议,开启全球精准医疗之路。
上一篇:美国诊断:不是I 期是IV期
 15
15
 1000+
1000+
 15
15
 8000+
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