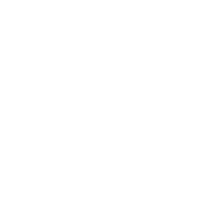追根溯源,癌症的本质是由于癌细胞变异而导致的疾病,而变异细胞的不同也导致了癌症种类繁多。不过P53细胞是一个例外,其存在于半数以上的癌症中。因此,如何更好的应对P35基因突变成为了海内外医疗机构的研究重点。近期,研究发现了一种靶向新药能够有效的应对抑癌基因P35突变,这或让更多的癌症患者受益并有效的延长生存期。
不久前,一款药物Eprenetapopt可能能打破p53没有靶向药的现状。在II期临床试验中,Eprenetapopt治疗52名携带p53突变的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患者和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有效率52%,37%的患者完全缓解[1]。
p53基因一直是肿瘤领域里的一个明星基因,一半左右的恶性肿瘤都携带有p53基因的突变。人们起初以为p53是一个促癌基因,后来才发现它是较为重要的一个肿瘤抑制因子[2]。
当细胞中DNA受到损伤时,p53蛋白就会被激活,通过下游的信号通路让细胞停止分裂,修复DNA损伤,在损伤无法修复的时候还可以让细胞凋亡,阻止癌症的发生[3]。p53突变失活后,细胞失去对DNA损伤的监控,很容易积累突变变成癌细胞。
而突变失活的p53,不但失去抑制肿瘤的功能,还会影响正常的p53蛋白,抑制其功能,进一步促进肿瘤的生成[4]。
p53突变不但会让肿瘤容易发生,还会让肿瘤更难治。比如血液系统肿瘤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MDS)和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中,携带p53突变的患者常常化疗效果很差,缓解期很短,尤其是p53双等位基因都突变的患者和核型复杂的患者,预后更差[5,6]。这些患者,即使进行了骨髓移植,也很容易复发[7]。
由于致癌的p53突变是其失活突变,要想靶向p53就得恢复p53突变的功能。药物研发上,想要抑制一个蛋白的功能容易,想恢复一个蛋白的功能却很难。就拿现有的靶向药来说,目前所有上市的靶向药都是靶向某一种癌蛋白,抑制其致癌功能,没有一种是靶向抑癌蛋白恢复其抑癌功能的。
恢复p53的功能虽难,但也有一些研究为这一目的指明了方向。一些潜在具有恢复p53蛋白功能的先导化合物已经被合成了出来[8],已经用于治疗AML的三氧化二砷(也就是砒霜)也被发现具有恢复p53功能的作用[9]。这些分子都能与p53蛋白中的半胱氨酸残基上的巯基作用。
Eprenetapopt正是根据这一思路设计的第一款p53靶向药,它在体内能结合突变型p53中的半胱氨酸残基,将其构象转化成野生型p53的构象,恢复p53的功能[10]。
在这次的II期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共招募了34名MDS患者和18名AML患者。他们均携带p53突变,平均年龄74岁,男性占48%,87%具有复杂核型,21%有p53双等位基因突变。研究所用的治疗方案是Eprenetapopt联合化疗药物阿扎胞苷。到试验结束时,有39名患者符合条件被纳入分析。
在MDS患者中,Eprenetapopt联合阿扎胞苷获得了62%的有效率,47%的患者完全缓解。中位响应时间和完全缓解时间分别达到了10.4个月和11.4个月,中位生存期12.1个月。
作为对比,先前的研究中,单独使用阿扎胞苷治疗p53突变的MDS和AML患者,中位生存期大约只有6个月,差不多是Eprenetapopt联合阿扎胞苷治疗的一半。
研究中,37%的患者出现了治疗相关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发生率与阿扎胞苷单药治疗时相似。还有40%的患者出现了治疗相关的神经不良反应,其中3例达到了3级不良反应标准。这些神经系统不良反应在停药5天内完全可逆,减少剂量后不再出现。
目前,FDA已授予Eprenetapopt联合阿扎胞苷治疗MDS的突破性治疗认证,和治疗AML的孤儿药称号,相关的III期临床研究也正在进行[11]。
尽管该靶向药物的临床治疗效果显著,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国内制度审批等原因影响,不少海外新药短时间内在国内无法上市。相反,美国作为全球的医疗大国,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的资源用于癌症新疗法、新药的临床试验研发。因此,国内治疗效果不好特别是病情进展到中晚期的癌症患者,可以联系盛诺一家报名海外临床试验,从而接触到更新的治疗方案来提高五年生存率。
参考文献:
[1]. Cluzeau T,Sebert M, Rahmé R, et al. Eprenetapopt plus azacitidine in TP53-mutated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 and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 phase II study by theGroupe Francophone des Myélodysplasies (GFM)[J].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2021: JCO. 20.02342.
[2]. Lane D, LevineA. p53 Research: the past thirty years and the next thirty years[J]. ColdSpring Harbor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2010, 2(12): a000893.
[3]. Joerger A C,Fersht A R. The p53 pathway: origins, inactivation in cancer, and emergingtherapeutic approaches[J]. Annual review of biochemistry, 2016, 85: 375-404.
[4]. Boettcher S,Miller P G, Sharma R, et al. A dominant-negative effect drives selection ofTP53 missense mutations in myeloid malignancies[J]. Science, 2019, 365(6453):599-604.
[5]. Bejar R,Stevenson K, Abdel-Wahab O, et al. Clinical effect of point mutations in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1, 364(26):2496-2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