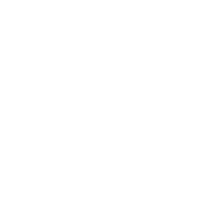如果把传统的膀胱灌注比作“猛火快炒”,药液进出匆匆,那么这项蕞新的国外研究干脆把火候调成“文火慢炖”——用一枚“椒盐脆饼”形的小装置(TAR-200),把化疗药在膀胱里慢慢“泡”足三个星期。
临床研究结果非常亮眼:82%的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对常规治疗已无效)肿瘤完全消失!
多数人在三个月内达成,近一半在一年时仍未复发。

TAR-200是一种用于治疗膀胱癌的实验性装置,由强生公司制造
把这条前沿消息放在中国的现实里看,意义更直观。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估算,2022年我国新发膀胱癌近9.3万例,是男性高发肿瘤之一;死亡超4.1万例,接近新发病例的一半。
接下来,我们用通俗的方式,讲讲这枚“脆饼”是怎么工作的、它可能改变什么、以及中国患者该如何正确看待这项新技术。
把药留在膀胱里更久,药效就能“泡”得更深?
这枚装置的学名叫TAR-200。
医生通过导尿管把它送入膀胱,它会在膀胱内缓慢释放化疗药吉西他滨,每个治疗周期停留三周,然后再取出或更换。研究团队的思路很朴素:药在膀胱里停留越久,渗透越深、杀伤肿瘤越彻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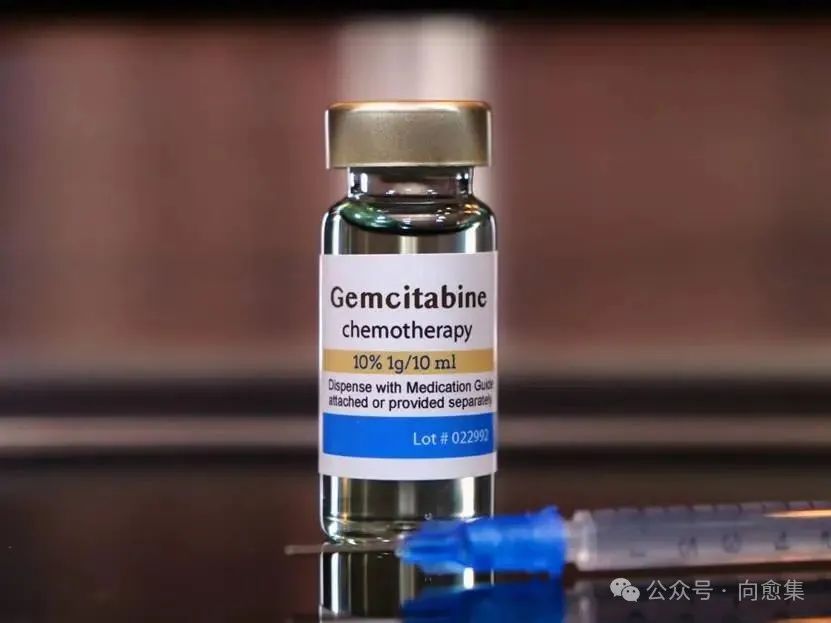
TAR-200可将吉西他滨以靶向、缓慢释放的方式直接输送到膀胱内
这并不是“天马行空”的想法。对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传统首选是卡介苗(BCG)膀胱内灌注免疫治疗,但30%-40%的患者初治无效或随后复发,往往被建议切膀胱(根治性膀胱切除)。
TAR-200的初衷,就是为这类对BCG“无应答”的患者提供保膀胱的替代路径。在这项研究中:
85例BCG治疗失败的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接受TAR-200治疗,其中70例(占比82%)达到完全缓解,多数在3个月内肿瘤就消失,近半数一年时仍未复发;
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尿频、尿急、尿痛、尿路感染等轻度尿路刺激症状,多在数周内缓解。
基于这些数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于2025年7月对TAR-200的新药申请授予优先审评——在6个月内完成审评,而非常规的10个月。
这对中国患者意味着什么?
先看“病情地图”。
膀胱癌中约80%是非肌层浸润性,这群患者理论上希望保住膀胱;但一旦对BCG无应答,过去的“金标准”常常走向切除膀胱——这是一台创伤大、并发症多、对生活质量影响显著的手术,需要尿流改道,终身随访。

膀胱是人体下腹部储存尿液的一个器官
我国卫健委发布的《膀胱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中,仍以“经尿道肿瘤电切+膀胱内灌注”为基础路径,并把BCG无应答患者的根治性膀胱切除作为重要选项之一。
而这,正是TAR-200可能“接棒”的位置:对于BCG无应答、仍局限于膀胱黏膜/黏膜下层的高危患者,它提供了一个药物保膀胱的新方案。结合我国现实:
高危亚型膀胱癌复发率高、进展风险大,治疗路径不顺时,患者很容易“走向切除”;
从流行病学看,我国每年近10万新发膀胱癌患者,4万+死亡,意味着保膀胱且降低复发的创新路径,公共卫生价值巨大。
当然,我们也要冷静:当前关于TAR-200的关键数据,主要来自样本量85例的研究,随访到1年给出了“近半未复发”的可喜信号,但更长期的持久性、对进展与生存的影响,仍需III期或更大规模研究来“盖章”。
FDA虽已优先审评,但是否获批、获批适应证范围以及未来在中国的可及性,都还有一段路。
谁可能更适合该装置?怎样用,风险如何?
根据目前披露与申报,以下是TAR-200蕞可能受益的人群:
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例如高分级、原位癌)
BCG无应答(包括BCG难治/复发等定义范畴)
病灶局限于膀胱黏膜/黏膜下层,尚未进展到肌层、未远处转移
有强烈保膀胱意愿,或不适合接受大手术的患者
治疗流程大体是:
门诊下通过导尿管置入TAR-200装置
TAR-200在膀胱内停留三周,持续释放吉西他滨
取出或更换,按周期重复
需要强调的是,一旦进展到肌层浸润或发生转移,TAR-200就不是合适的治疗;此时要遵循指南,考虑手术、放化疗、免疫/靶向等系统治疗策略。
别只盯着“新器械”:评估与团队,比技术本身更重要
在真正把某个方案写进你的病历前,精准分期与分层、多学科讨论(MDT)是“保膀胱”的安全阀。

(来源:摄图网)
MDT的要义,不是让患者“围着医生转”,而是“医生围着患者转”:内科、泌外、病理、影像、麻醉等科室把病例合在一张桌子上,对病理、影像、风险进行逐项核对,再定方案。
对肿瘤治疗这类重大、复杂、不可逆的决策,二诊意见几乎是“刚需”。哪怕你已在权威医院拿到一套方案,也建议至少再做一次独立评估;因为一旦路径选错,补救空间往往非常有限。
更何况,肿瘤不是“一夜长成”,在充分检查、明确病理的前提下,用几周时间把诊断捋清、把方案开准,远比“匆忙上手术台”要安全得多。
把眼光拉回到TAR-200:它很有潜力,但不等于“人人适用”。正确的打开方式,是在MDT框架内把它与BCG、经尿道电切、(必要时)切膀胱、乃至其他新疗法进行并列比较,看病理、看风险、看个人诉求,最后再决定谁更合适。
结语:
医学的进步,常常不是“天外飞仙”,而是把“老药新用”“看似小改动”做到极致——把药留在正确的位置、足够久,就可能带来质变。
TAR-200之所以令人振奋,不只是因为“82%完全缓解”的漂亮数字,更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在标准疗程失败后仍能保膀胱的现实路径。
对中国患者与医生而言,务实的期待是:跟踪更长期数据与监管结论,有条件的中心积极参与临床试验;同时,把它放进规范化评估与多学科决策的“工具箱”,让每位患者都能在安全边界内,争取到更少的切除、更好的生活。
参考来源:
1.New pretzel-shaped device cured 82% of bladder cancer patients — most in just 3 months(装置、疗效、停留时间、副作用与FDA优先审评等关键信息)。
2.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 GLOBOCAN 2022 中国癌症概览(中国膀胱癌发病与死亡数据)
3.Int J Mol Sci. BCG-Unresponsive NMIBC: Current Treatment Landscape…(NMIBC约占新诊断膀胱癌的80%,BCG无应答的现状与治疗困境)。
4.国家卫生健康委:肿瘤和血液病相关病种诊疗指南(2022年版)(含《膀胱癌诊疗指南》发布信息)
【盛诺一家】成立于2011年,是国内领先的海外医疗咨询服务机构,至今已为近10000个患者家庭提供出国就医服务,重点涵盖癌症、心脏病、罕见疾病等重疾领域。凭借专业、贴心、高效的服务,盛诺一家赢得了99%客户好评率!
📌为什么出国就医患者选择盛诺一家?
- 官方资质:与美国、日本、英国近50家TOP级医院签署官方合作协议,搭建全球医疗服务网络
- 专业可靠:咨询服务团队成员70%拥有医学背景,包括医学院博士、三甲医院医生、资深医学翻译
- 一站式服务:在全球设有15个客户服务中心,保障从国内到海外全流程、高品质的服务质量
- 客户至上:推出48小时冷静期、风险告知书、医疗费用“零加成”等措施,保障客户权益
- 专属折扣:通过本公司预约出国就医的患者,可额外申请5%–40%的医疗费用减免折扣
👉如果您或者家人需要出国看病,可拨打免费咨询热线 400-855-7089,或通过 盛诺一家官网 预约咨询!